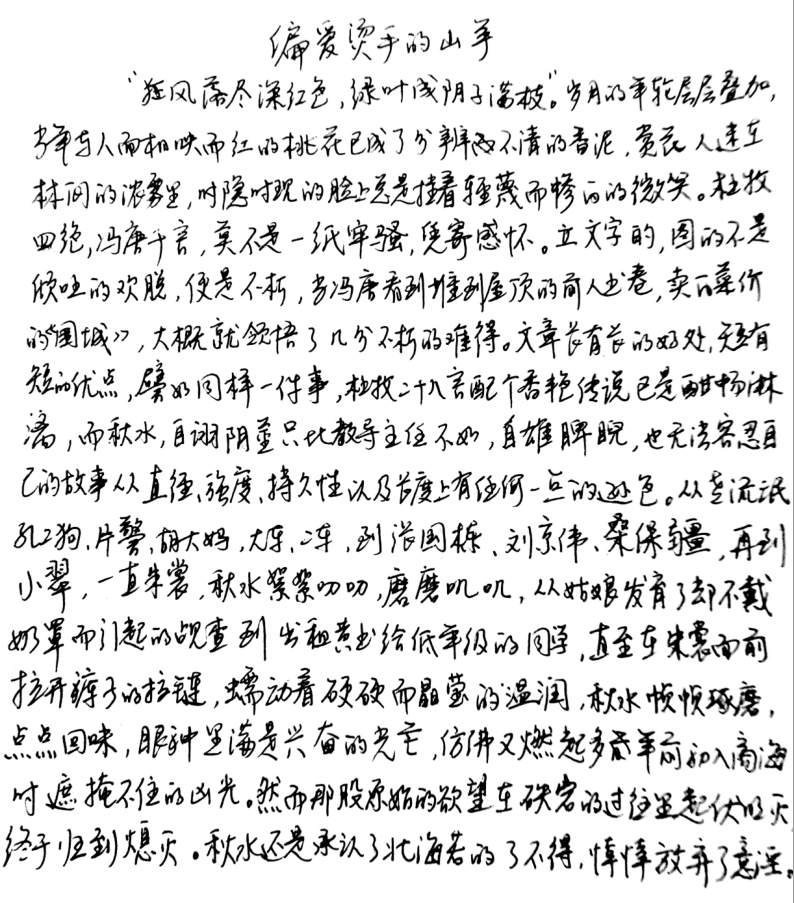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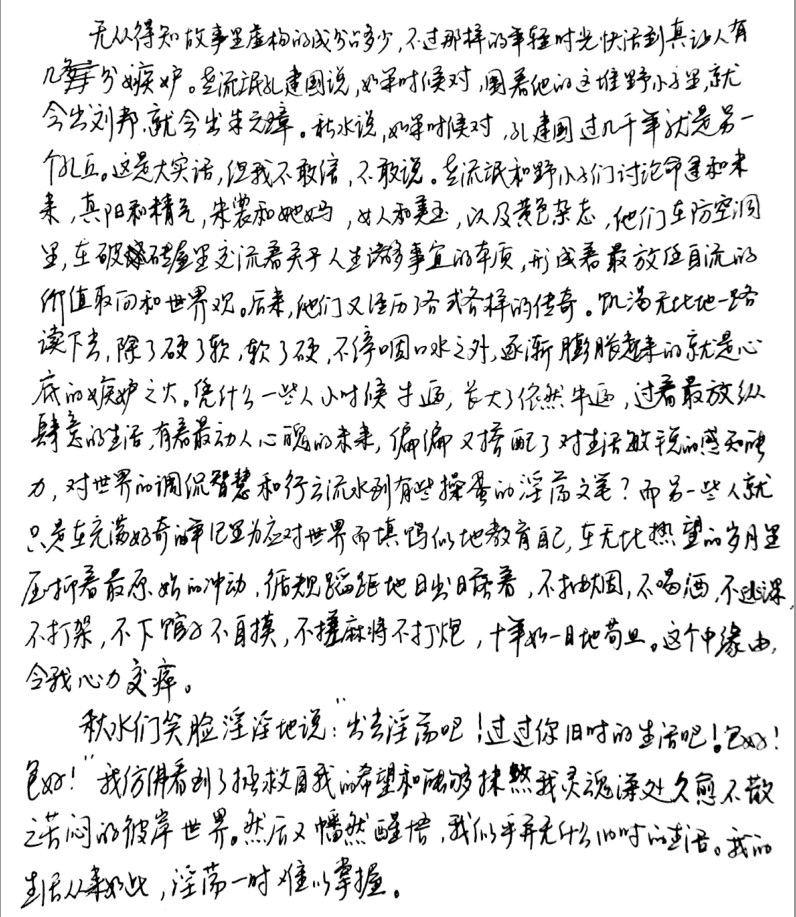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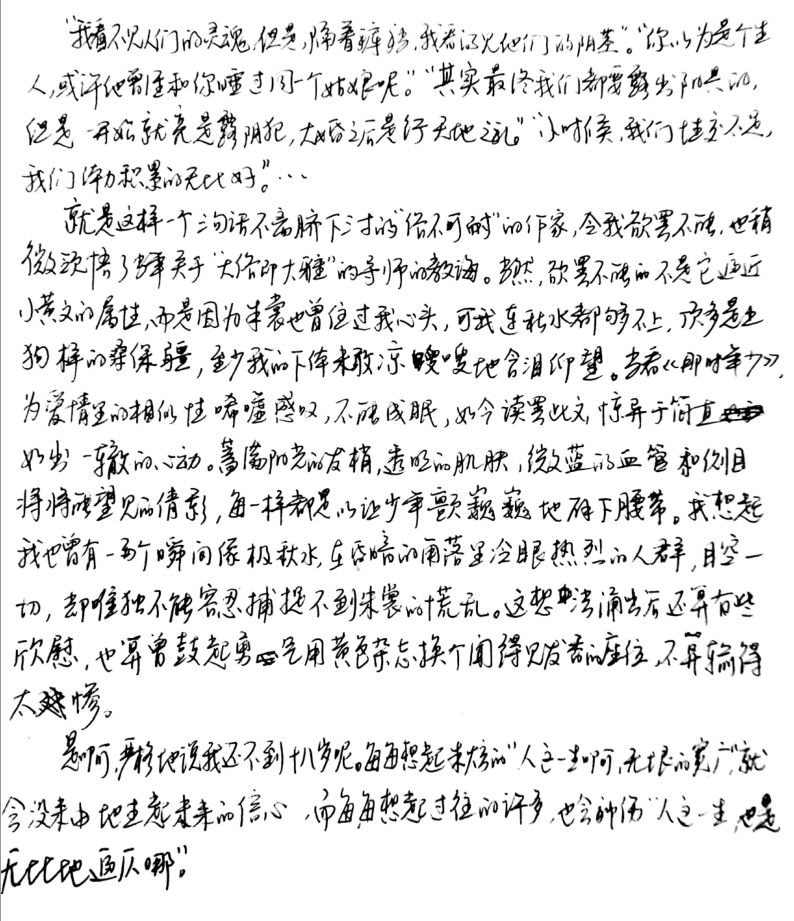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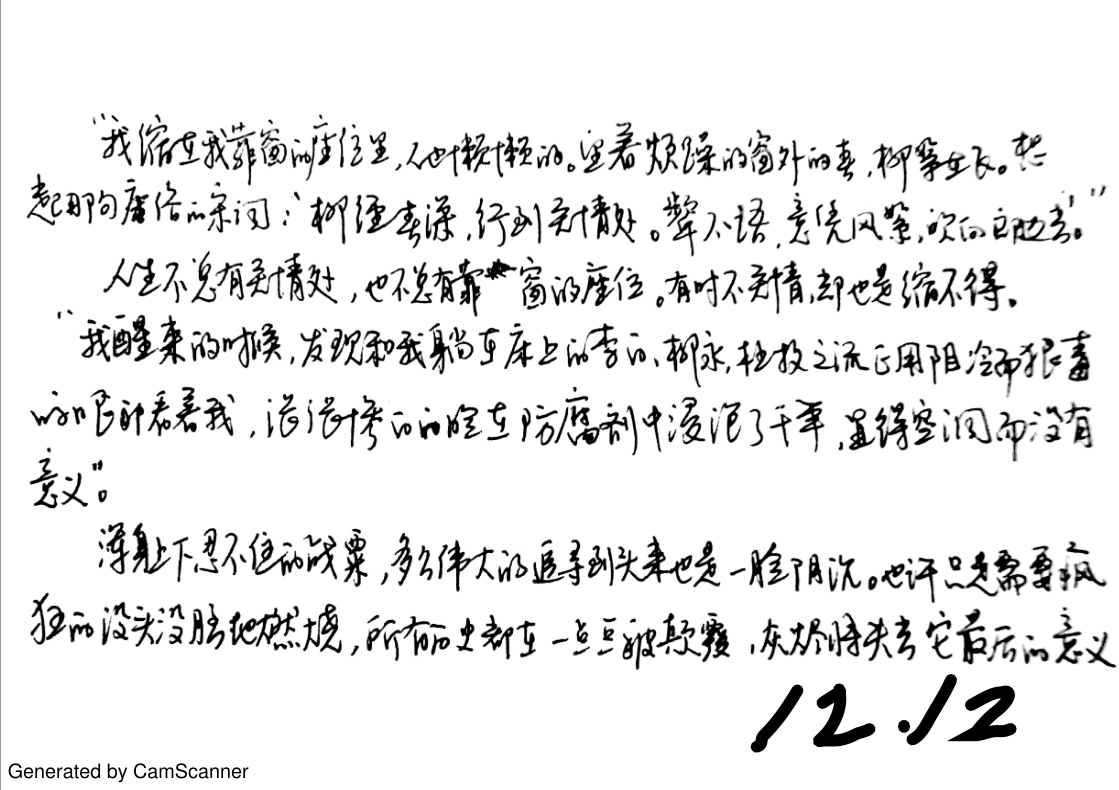
摘抄
“事后想来,如果时候对,如果老流氓孔建国会些医术,被当权部门用钉子钉死在木板上,过几百年就是另一个耶稣。如果老流氓孔建国会说很多事儿逼的话,被刘京伟、张国栋和我记录下来整理出版,过几千年就是另一个孔丘。 "
“他说,如果时候对,围着他的这堆野小子里就会出刘邦,就会出朱元璋。”
“我让老流氓孔建国高兴,因为我能迅速领会每一种精致的低级趣味,别的野小子还在做思想斗争的时候,我已经笑得很淫荡了。老流氓孔建国说我也让他头痛,因为我记性太好,老流氓孔建国不得不绞尽智慧回忆起或创造出新的趣事。这件事随着老流氓孔建国记忆力和创造力的减退以及我的不断成长而变得越发艰难。”
“根据老流氓孔建国回忆,当老流氓孔建国有一天不得不怯生生地开始重复一个黄故事的时候,他在我的眼珠滚动里看到了一种他不能鄙视的鄙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有回过防空洞课堂。 "
“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讨论,我说刘京伟眼里有光、下身总是硬硬的、元气充盈,将来一定了不起。他骨子里的贪婪常常体现在小事情上,一根冰棒,他会一口吞到根部,再慢慢从根部嘬到尖尖儿,第一口就定下基调:从根到尖,涂满他的哈喇子,全部都是他的。老流氓孔建国却说他神锋太俊,知进不知退,兴也速、败也速,弄不好,还有大祸,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军阀的胚子。我听了糊里糊涂的。老流氓孔建国又说,我也很贪婪,眼里也有光,但是我的眼底有很重的忧郁。我更糊涂了,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就嚷嚷:“你丫别扯淡了,我平面几何考试怎么及格还不知道呢。你再胡说,我到胡大妈那儿告你企图鸡奸。” "
“楼下老头子们讲,梦里的都是妖魔鬼怪,吸走的都是真阳。真阳没了,眼珠子也就不转了,鼻涕快流进嘴角的时候也不能及时地吸进鼻孔了。 "
“他们说起他们过去的故事,我总是将信将疑。 "
“没有法子,男人只有自己出门找水喝, 怕人家不乐意给, 随身带上了刀。 "
" 黑胖子的老婆说黑胖子原来在炮兵部队上是厨师班长,从来只负责偷吃不管干活。我想,没有比黑胖子过去的职业更悲惨的了,戴绿帽子、背黑锅、看别人打炮。
"
“明里不见人头落,暗中叫你骨髓枯。刘京伟和张国栋认定,随着时间流逝,我即使不会精尽而亡,也会渐渐出落成为一个没有出息的笨人”
“她可能不是同谋,只是阴谋的一部分。 "
“我看不见人们的灵魂,但是,隔着裤裆,我看得见他们的阴茎。”
“我当然也有理想啊。我的理想是娶最漂亮的姑娘,写最无聊的文章,精忠报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你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不娶你娶谁呀?” "
“你以为是个生人,或许他曾经和你睡过同一个姑娘呢。” "
“桑保疆是倒尿盆长大的,这个,他懂不了。
"
“其实我们最终都是要亮出阳具的,但是一开始就亮的是露阴犯,大婚之后的是行天地之礼。 "
“我的长相平庸而粗糙,但是我的内心精致而细腻。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说,别看我长得象个杀猪的,其实我是个写诗的。 "
“那个写诗的晚上,我速读《诗经》,跳过所有祭祀章节和不认识的文字,明白了“赋比兴”和“郑风淫”、最大的写诗诀窍就是找到心中最不安最痒痒的一个简单侧面,然后反复吟唱。那个写诗的晚上,我写完了我这辈子所有的诗,之后再也没有写过一句,就象我在十六岁至十八岁期间耗尽了我对姑娘的所有细腻美好想象,之后,所有的姑娘在我的眼里都貌美如花。”
“我以前总是纳闷,街面上日日在自己面前飘然而过的那些美若天仙的姑娘们回家后都和谁睡觉。观察过朱裳父母之后我清楚了,就是和朱裳爹这种人。这种人坐不出龙椅和马扎的区别,赏受着上等的女人,无知无觉,问心无愧,如得大道。否则的话,对绿帽子的担心,就会让他少二十年阳寿。 "
“美人在专心开车,不象平日里一样过分专注于自己的美丽,所以格外好看。 "
“后来,我学了心理学,才感觉到,少年时期很多美好想象都是境由心生,没看过猪跑,更没吃过猪肉,把对凤凰的想象都拽到母猪身上了。 "
“我一觉醒来,大吼一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想起过去创作这首打油诗的诸葛亮,在那个叫南阳卧龙岗的地方,种田、读书、钱多的时候叫鸡、钱少的时候手淫,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
“是孔明就要论天下,是关公就要舞大刀”。刘京伟和张国栋听到,一定会加盟,老流氓孔建国听到,一定会加盟,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
“现在的空气脆而冷,就在这种天气里,一个案件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好人坏人正义邪恶变得混沌不清,各种关系纠缠在一起,不是案件,而是一个阴谋。女孩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阴谋里起的作用极其重大而微妙,朱裳的意义更加隐涩。”
“好象忽然一夜间,所有男生都想有一双名牌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仿佛一双名牌鞋能添无数牛逼和小女生的目光。在之后的进化过程中,男生变成男青年,中年男子,老头,这双名牌运动鞋也随着变成名牌手提电脑和名牌山地车,一米七八一头长发的妖艳女友和宝马Z3以及郊区豪宅,一米六零胸大无脑柔腻软滑的十八岁女孩和明紫檀木画案以及半米长的红山玉龙形钩,但是,给予不同阶段的男性生物,同样的渴望、困扰、狂喜和无可奈何。 "
“刘京伟是个头脑灵活但是无比简单的人。他短暂的一生都在追求牛逼。不同阶段,追求不同的牛逼,所有追求到的牛逼加总就构成了刘京伟短暂而牛逼的一生。 "
“第二天,刘京伟请我和张国栋在朝阳门外的桥头酒店吃五块一斤的三鲜饺子,他吃得很少,两手抱着他新买的白地蓝钩高帮耐克鞋,那双鞋用鞋带串在一起,跨在他脖子上,左脸边一只,右脸边一只,每只都比他的脸大,比他脸白。刘京伟两眼望着天花板长久沉默,他忽然说:“牛逼,牛逼啊。”
“后来,刘京伟的激素水平发育到觉得有个妖艳女友是牛逼的。刘京伟对我说:“我没有你会臭侃山,没有张国栋长得清秀。我怎么办呀?”我说:“总有办法的。”张国栋说:“再生一回吧。”刘京伟说:“张国栋你闭嘴。只要我活着,就会比你牛逼。你再清秀也是一堆清秀的狗屎。我和秋水说话。秋水,你有一点我特别佩服,你的自制力极好。你一个人呆的时候该看书也看书,该修炼你的文字就修炼你的文字。我也要在一个指定的方向上使力气,我也要修炼。”他于是修炼了一身腱子肉,条条块块,是姑娘都想摸。他冬天也穿紧身短袖,像个脱了皮的蛤蟆。为了长肌肉,他每天不吃饭,在最短的时间喝二十五个生鸡蛋。”
“。张国栋问刘京伟,这样练,阳具也跟着变大吗?刘京伟说,不是,反而缩小,因为血都充到其他大块肌肉上去了。张国栋说,那我就不练了。我说,锻炼不同肌肉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反复充血,你应该多看黄书,但是要保持不射。张国栋说,自摸行吗?刘京伟看了看我,我们同时说,行,可你丫能保持不射吗?”
“再后来,刘京伟的大奔里没有姑娘香水味了,刘京伟欢快地对我说:“你知道现在最牛逼的是什么吗?是雇哈佛大学毕业的MBA。我把姑娘们都打发了,雇了三个今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MBA。”
“这时候的女孩个个可看。即使最丑的姑娘也有动人的时候。
"
“后来的后来,我在老流氓孔建国的教导下玩玉。老流氓孔建国说:“你早上睡醒之后,摸摸下体,如果已经不是一柱擎天了,说明你的真阳已经不足。有些人在三十发现,有些人四十。这时候,你对真善美的兴趣就应该从姑娘转到玉。处女是新玉新工,贼光扎眼。二十几岁是清初件,康乾盛世呀。三十几岁是宋元明,‘明大粗’。四十来岁是商周古玉,铅华洗尽,没有一丝火气,美呀。玉好像姑娘,也需要陪,需要珍爱,需要一日三摸搓,可以戴,可以显摆,可以放进被窝儿。玉比姑娘好,不离不弃,不会逼你一夜三举,还可以洗洗留给儿子。算了算了,别老想着朱裳和翠儿了,昨天我在古玩城小崔那儿看见一个商早期的圆雕玉虎,青玉,十多个厘米长,沁色美极了,太少见了,图谱上有片儿的,够上拍卖会进博物馆的。准备几万块钱,咱们明天把它拿下。”
“不要老拿你的大油手在玉上摸来摸去,玉会污的,污了就再也干净不了了。真正的盘玉,是戴在身边,用身子煨着,用脑子想着,把你意淫文字的功夫用到这儿来,一两个星期用热水泡一下,用粗白布擦。不要老拿你大油手摸,糟践好东西。””
“我们不要音乐要叫喊,
我们不要道理要金钱,
我们不要先生要混蛋,
我们不要女生要天仙。
为什么越用功的女孩脸蛋越苦?
为什么我越想越糊涂?
为什么几千年都过去了,
还没有另一个秦始皇烧干净书?
姑娘你仰头总是绷着漂亮的脸,
仿佛要沾你的一定是个款,
为了心理平衡我想问几遍,
你是否也天天大小便?”
"
“如果从小长到大是个电子游戏,游戏里有好些凶险的大关卡,最早是如何应对父母,如何和兄弟姐妹相处,如何和发小一块玩耍,然后是如何对付摆在你面前的象朱裳这样天生狐媚的姑娘,如何对付混蛋的教导主任和白痴数学老师,然后是每个人都有的老板和老婆,然后是整日呼啸的小孩、父母的老去。面对朱裳这个题目,我们没有一个男生答对了。有些人给自己一个借口,反正也试过了,有些人索性忘记了,有些人找个眉眼类似的,反正没人知道正确答案,所有人都在游戏里过了关,可能编游戏的人是个逻辑不清的人吧,很少较真。”
" 在书里倦了,合上书,找个晦涩的角度看朱裳,我觉得明目爽脑,仿佛夜里读书累了,转头细看窗子里盛着的星星。过去没有电视和互联网,我们和古人一样,看自己的身体,看天空的星星,看同桌的姑娘,在简单中发现复杂的细节和普遍的规律。 "
“关于朱裳,我该学习多少次呢”
“我要老到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这些记忆?我是学医的,我知道即使失去双手,双手的记忆也还是在的”
“。”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来藏着的一包大前门,反锁了宿舍门,点上一根给张国栋,自己再点一颗。我坐在我床铺前的桌子上,向张国栋表白,希望他能理解:
“我坐在朱裳身边,如果天气好,窗户打开,风起来,她的发梢会偶尔撩到我的脸,仿佛春天,东三环上夹道的垂柳和骑在车上的我。” 我看着张国栋,接着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了。”张国栋收起书包,“杂志你先看吧,借你的,不是送你的呦。”
“张国栋说,他还记得我面对黄色杂志的表白,记得东三环上夹道的垂柳和朱裳的相似,这个意象对他很重要,等他挣够了钱,他一定写个关于这个意象的本子,然后拍个不赚钱的片子。”
“在张国栋摊了一堆黄色杂志,和我交涉换座位之后,他时常找我聊天。话题总是围绕女人,特别是关于朱裳。在我漫长的求学过程中,男生和男生之间时常进行这种交流,题目多数是关于女人,偶尔涉及考试和前程。如果把考试的定义扩大,女人也是考试题目,我们长久地讨论,以期充分理解题目,上场的时候争取马虎过关。刘京伟从来不参加这种讨论,他说我具备一切成事的素质,只是想得太多。刘京伟不喜欢念书,不喜欢考试,他喜欢他的一切都是标准答案。刘京伟通常采取的态度是:“我就这么做了,怎么着吧?”他看见我茫然不解,就举例说明:“比如你喜欢一个姑娘,就按倒办了,丫不开心,就杀,就走。如果心里还是喜欢,下次再遇见,再奸,再杀。”我说这些道理太高深,无法顿悟,我天分有限,不念书不考试就无法懂得。刘京伟预言,他都死了,我的书还没读完。刘京伟一语成谶,我参加他的葬礼的时候,关于卵巢癌发生机制的博士论文才刚刚写完初稿,答辩会还没有安排。 "
“他说我具备一切成事的素质,只是想得太多”
“姑娘又不是阿拉伯数字, 不具有可比性。 玫瑰好看, 做汤肯定没有菜花好吃。”
"
“只是干净?”
“你以为干净简单?我觉得你张国栋让女孩感觉舒服,你以为这‘舒服’二字简单?”
“就是呀,我这种气质,很难培养的,每周都要洗澡,每天都要刷牙。还有,要看书,多看书,‘腹有诗书气自华’。还有,要多思考,否则就肤浅了。绝不简单。”
“追她的人已经够多的了。我不喜欢锦上添花。” "
“就是。好象是个男的就应该想和她有一腿似的。我都有点压不住邪念了。不过,多点追的才有意思,横刀夺爱,方显英雄本色。” "
“持续学坏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呀。可惜不是什么好烟,‘红梅’。本来第一支应该是支好烟,就象童男子破身之后通过政治思想学习,再次成为童男子,再次破身应该是个好姑娘,至少也应该和朱裳差不多吧。” "
“书之外,还有别的要懂的东西。 "
“学抽烟为了学坏,
学坏为了学习长大。
学习长大得厌恶爸爸,
再杀死他。
学习长大得爱上妈妈,
再抛弃她。” "
“你这么抽烟纯属浪费,”张国栋深吸一口烟,吞进肺里,再慢慢地让烟一丝丝地从鼻孔飘出来,青烟曲折回转散入周围的黑暗之中。 “想上就别憋自己。你有戏。”
“是么?”
“她喜欢你。”
“为什么?”
“你喜欢书,读得仔细,你有时候就是你喜欢的书。你能迷上你的书,别人也会迷上你。” "
“你说别人的事总是出奇的明白,遇到自己的事总是嫩。这事呀,你试试就知道了.就象有些事不用教,上了床自然就会了。再说你也没骚扰过小姑娘,也没少被小姑娘骚扰呀,怎么一到朱裳这儿就发木?咱们学校躲在树后面看你的姑娘不比原来躲在山洞里流着口水等着吃唐僧肉的妖精少。” "
“我想起我的小屋。周末回去,胡乱填几口饭,反锁上门,世界就和我无关了。拉上窗帘,大红牡丹花的图案就把所有光线割断,包括星星。打开台灯,昏黄的光线将满溢在小屋里的书烘暖。书从地板堆到屋顶,老妈说,书上不省钱,想看什么就买什么,读书多的孩子孝顺。书不像古董,不是世家,省省也能请回家最好的。我和我姐姐站在琉璃厂中国书店高大的书架前,我问她,妈给你的钱够吗?我姐姐说,够。我对售货员说,我要一整套十六本《鲁迅全集》和一整套二十五本《全唐诗》。我问售货员,近百年是不是鲁迅最牛逼了,近两千年,是不是唐诗最牛逼了。”
“我摆开几个茶杯,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就静静地坐在对面。倒上茶,千年前的月光花影便在小屋里游荡。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已经坐在对面了,他们的文字和我没有间隔。我知道他们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们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们绝不知晓的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泪流满面。第一次阅读这些人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以伦比,他们的灵魂像是一碗豆汁儿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让他喷涌而出更重要,比我第一次在慌乱中进入女人身体看着她的眼睛身体失去理智控制更重要”
“我第一次阅读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比我第一次解剖大脑标本,对我更重要。我渴望具备他们的超能力,在我死后千年,透过我的文字,我的魂魄纠缠一个同样黑瘦的无名少年,让他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我修炼我的文字,摊开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淡绿色,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钢笔在纸上移动,我看见炼丹炉里炉火通红,仙丹一样的文字珠圆玉润,这些文字长生不老。我黑瘦地坐在桌子前面,骨多肉少好像一把柴火,柴火上是炉火通红的炼丹炉。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就像朱裳的美丽和朱裳没有太多联系,我和朱裳都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朱裳的美丽,巫师的声音,有它们自己的意志,它们反过来决定我们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
“我对张国栋说:“我的屋子太小了,床上的书把我都快挤得没地方睡了。已经放不下别的了。” 杜牧,李白、劳伦斯、亨利米勒已经坐在对面了,朱裳坐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就先追了?我可是跟你商量过了。”
“好。需要的话,我替你写情书,送小纸条。如果人家对你有意思,我把座位让给你。” "
“从现在看来,我和朱裳的关系是由短暂的相好和漫长的暧昧构成。”
“小时候,我们性交不足,我们体力积累得无比好,”
“那时候,我和朱裳从天安门走到东单走到白家庄,北京夏天的白天很长,在半黑半白中,我们在43路车站等车,说好,下一辆车来了就分手。来了无数个下一辆,好多人下车,好多人上车,好多人去他们要去的地方。在等待无数个下一辆的过程中,我拉着朱裳的手,她的手很香。朱裳看着我的眼睛,给我唱那首叫Feelings的外文歌曲,她的头发在夏天的热风里如歌词飞舞,她说我睫毛很长。后来朱裳告诉我,她之后再没有那么傻过,一个在北京这样自然环境恶劣的城市长大的姑娘怎么可以这样浪漫。我说我有很多回想起来很糗的事,但是想起,在我听不懂的外文歌曲中,握着将破坏我一生安宁的姑娘的香香的手,永远等待下一辆开来的43路公共汽车,我感到甜蜜和幸福。”
“很多个小二锅头之后,朱裳说,在中学,她听不进课的时候、累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看我,认为我和别人不一样。教材、教参、习题集堆在我桌子上,堆成一个隐居的山洞,挡住老师的视线,我手里却常年是本没用的闲书。她觉得我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一个与她爸爸略相象的读书人。真正的读书人如同真正的厨子、戏子、婊子,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对所钟情的事物的痴迷。书中的女人秀色可餐,书中的男人快意恩仇。书外如何,与真正的读书人无关。她喜欢看我脸上如入魔道的迷离,如怨鬼般的执著。我说:“是不是我长得象你爸就能娶到你妈那样的?”朱裳说:“我当时是年幼无知,看走了眼,其实只是你太瘦了,招眼,容易让人心疼。”
“我对朱裳说,女人或者复杂或者单纯,都好。但是,复杂要象书,可以读。简单要象玉,可以摸。当时的朱裳也不让解扣子,也不让上手摸,我能干什么呢? "
“她坐在我旁边,忍不住会在我专心念闲书的时候看我。她感觉到与我本质上的相通:“一样的寂寞,一样的骨子里面的寂寞。这种寂寞,再多的欢声笑语,再迷醉的灯红酒绿也化解不开,随便望一眼舞厅天窗里盛的星空,喝一口在掌心里的隔夜茶,寂寞便在自己心里了。仿佛他打开一本闲书,仿佛我垂下眼帘,世界便与自己无关了。这种寂寞,只有很少的人懂得。”
“哥哥们看到朱裳小妹妹听得泪流满面,脸上珠串晶莹,不禁心惊肉跳,明白这个小妹妹心中有股大过生命的欲望,今生注定不能平凡。”
“最出色的一个看她的眼神开始不对了,试探着和她谈一些很飘渺很抽象的事。她开始害怕,大哥哥们不可爱了。 "
“安全第一,男孩第二”,她们的父母教育她们。 "
“翠儿除了演戏之外,不化妆,她说上妆毁容,就像写东西折寿一样”
“梯子当时跟我阐述,她年纪还小,还没想清楚是出国颠覆美国腐朽的资本主义还是留在国内大干社会主义,还没想清楚是青灯黄卷皓首穷经搞学术还是大碗吃肉大秤分金搞生意,所以洋书生和土大款都要交往。我说,同意,注意时间安排,注意身体,努力加餐饭。最后梯子选择了资本主义腐朽生活,到了美国一年后拿了绿卡,就和陕西洋考古离了婚,说是在美国一年到头吃不着有土腥味的活鲤鱼,却要整天睡有土腥味的老公,不靠谱。梯子马上找了个美国老头,有钱,有大房子,有心脏病,阴茎短小但是经常兴奋。老头是用直升机把梯子娶进那个大房子的,我见过婚礼上的照片,长得像大白胡子的圣诞老人,梯子皮肤光滑滋润,但是表情还是很坚毅。第一次上床,梯子说,就知道了老头的斤两,梯子还说,不是吹牛,如果她愿意,和老头隔着一千英里,电话性交,她能让老头心脏病发作,死在去医院的救护车上,脸上还充满淫荡的笑容。老头就是这样死了,梯子带着美国护照和天文数字的资产回到北京,对我说:“我从小都找比我老比我成熟的,追求前进追求光明,现在我要反过来了,你说,我是不是老了。”我说:“怎么会,你的肌肉还结实,腿上毫无赘肉。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你还是易如反掌。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又比我们早好几步领导了潮流。””
“我总对我的女朋友说,你是舞后,你玩儿你的,我一点都不在意,我替你在这儿看管大衣。我在角落里看我的女友在舞场里旋转,她的头发盘起来,她笑脸盈盈,她汗透春衫,我觉得她比和我在一起的任何时候都美丽。 "
“你乐感好,听着音乐、跟着我就好了。” 张国栋一笑,朱裳后来告诉我,张国栋有一种不属于淫荡的笑容,很容易让女孩想起阳光。”
“我有一种理论,物质不灭,天地间总有灵气流转,郁积在石头上,便是玉,郁积在人身上,便是朱裳这样的姑娘。玉是要好人戴的,只有戴在好人身上,灵气才能充分体现。女人是要男人抱的,只有在自己喜欢的男人怀里,灵气才有最美丽的形式。 "
“对浅吟低唱、春情萌动不感兴趣的一小堆男生正扎在一起猛吃剩在桌子上的公费瓜果梨桃、花生瓜子,大谈现代兵器、攻打台湾及围棋。”
“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张国栋觉得,“文革”是一种节日。人可以活在天地间,可以打架,可以泡妞,可以象个好汉,名正言顺。男孩从打架中能学到不少东西:忍让,机智,必要的时候诉诸暴力。仿佛四、十万年以前,北京人还住周口店的时候,打架能让你获得猎物,泡妞能让你的姓氏繁衍。现在的混混只能学学港、台的小歌星,穿得光鲜亮丽,将来不会有大出息。 "
“人性是多么堕落呀!”
“我是多么喜欢堕落呀!” "
" “回头再买十串羊肉串,多放孜然,多放辣椒,一人一瓶啤酒, 一边吃喝一边回学校。”
“啊, 生活!”
“太资产阶级情调了,小资”
“我们并肩走在大街上,我看见,路灯映照着张国栋、刘京伟、桑保疆的脸,他们脸上的粉刺大红大紫,灿若春花。侧头,天上是很好的月亮,好象什么都知道似的冷冷地瞧着。我们什么都不多想地朝前走,前面是不再刺骨的风. 将来是什么都会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武侠小说上说,鲜衣怒马,年少多金。我们兜里各有三、五块钱,年轻真好。
而且,我们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姑娘。 我们手拉着手,像南北朝那时的同性恋一样,在大街上走。 "
“张国栋没呆多久就回来了,理由和几十年前毕加索的一样:艺术只有在东方,在中国和日本”
“张国栋在学校兼教职,他写信告诉我,原来姑娘也像庄稼和瓜果梨桃一样,每年都有新的一拨儿,新的一拨儿不见得比老的一拨儿难吃。”
“你们是不是皮肉发紧呀?” 我说”
“体育老师是个简单而纯朴的人,他挣很少的工资,一天三顿吃学校的食堂,最大的乐趣是帮助女生练习鞍马或是单杠等体操项目,他有一双温暖而肥厚的小手。孔丘说:天下有道,丘不与之易也。意思是,你牛逼,我也牛逼,我不拿我的牛逼和你的牛逼换,我不羡慕你。从小到大,我认真羡慕过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体育老师,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姑娘屁股摸,特别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物质贫乏,冬天唯一的新鲜蔬菜是大白菜。另一个是我的外科教授,他主攻乳腺外科,每天早上出诊,诊室里都是小一百对焦急地等待他触摸的乳房。 "
“教导主任常说的话是:“自然给孩子以身体,而我们塑造他们的灵魂。”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感到可怕,感到的是巨大的责任与成就。 "
“不建学校,就得多建监牢。学校人少,监牢中的人就会多。学校办得差,监牢中就会人满为患。”他在教师会上讲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自己象个将军。“中学生,说到底还是孩子。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阶段,象一块未琢磨的璞玉,未着色的白纸。不是他们缺少问题,而是我们缺少发现。”
“在教导主任眼里,怎么可能没问题呢?就象有些花要香,有些雨要下,有些娘要嫁一样,有些人从小注定不安分。 "
" 我们一起扑上去看,果然是一等奖。我当时毫不怀疑,我这辈子都挣不到五百元钱。”
“张国栋从骨子里瞧不上他,觉得象他这样一个面白无须,爱打小报告,好色却绝对作风严谨的人应该生活在那个太监属于正当职业的年代。”
“张国栋跟我讲过,三楼男生厕所第二个蹲坑的门上有两行字:“到哈佛读书,做朱裳老公。”
张国栋说:“咱们班长理想远大。我认得他的字。俗甜。”
“你的理想呢?”我问。
“挣钱。还有 ……”
“什么?”
“如果我和咱们班长的理想都实现了,我就尽全力让他戴绿帽子。开了奔驰600到他家楼下,用手机和朱裳叙旧。不急不燥,慢慢地聊。”
“大地一片静寂,除了我的呼吸和朱裳的心跳。一定要绿化了他,让他绿透了心,让他绿得萎而不举、举而不硬、硬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不射、射而不能育。”
“被迫满大街找电线杆子,顺着上面的广告钻胡同找老军医,最后受骗上当,一针下去再也抬不起头。然后和他的女儿混熟,去迪厅、歌厅、饭店、酒吧……见尽物欲横流,让她一回家就觉得家里憋气,看见她爸就憋气,有空就质问朱裳‘您为什么让这个人成了我爸爸?’……” "
“但是对于我这种天赋好、后天训练又严格的厚脸皮没有多少效果。”
“在翠儿面前,只有在翠儿面前,我停止思考,我的小弟弟替代我的大脑,全权主导我的行为。”
“我缩在我靠窗的座位里,人也懒懒的。望着烦躁的窗外的春,柳絮在飞。想起那句庸俗的宋词:“柳径春深,行到关情处。颦不语,意凭风絮,吹向郎边去。” "
“朱裳在,有两、三里垂柳堤岸就够了。“行到关情处”便是走到动情处了。手不必碰,眼不必交,只需两个人慢慢走就好了。有些心思,想不清,分不明。就象这酿在春光中的柳絮。有些心思也不必说出口,也不必想清楚,好在有柳絮。柳絮会带着柳絮一样的心思到她的身边去的,让她一样地心乱、心烦,一样的不明白。 "
“我、张国栋、刘京伟的步子放慢,朱裳聊了几句,一脸的不高兴。平时,朱裳虽然不爱说话,但从没有把不快堆在脸上。
我停了下来。张小三后来说,他很少看见我的眼睛里充满这种凶狠躁戾之色”
“你也上医院去看看吧。”朱裳后来说,她搀住我的手当时碰到我的单衣,她记得我的单衣下面的肌肉坚硬如石。 "
“老流氓孔建国早讲过,秋水的心术正不了。”
“或许自己真是不行了,连“酒色”都不行了,还有什么行的呀?真是对不住老流氓孔建国的教诲。 "
“人的脊柱里有盏灯,一杯“二锅头”沿着脊背下去到脊柱的一半,那是人的真魂儿所在的地方,一团火焰就燃烧起来了。啤酒要柔的多,要几瓶,时间要更长,灯也点不了太亮,飘摇着,就象一盏破油灯。油灯里的世界与白天里的不一样,与无光的黑夜里的也不一样。世界更加真实而美丽。”
“我没怕过什么人,也没信过什么。但我相信我将来会富,会成为一个有钱人。是不是男人就不该真的爱上什么人?就该搂完抱完心里什么也不剩?这样才能睡得着,吃得香,说起话来才能不顾忌,干起事来才能特玩命,才特别特别地象个好男人?这样,对,这样,就有许多女孩来喜欢你,然后你在搂完抱完心里什么也不剩。难道喜欢就是因为你不能放开了去喜欢?真他妈的见鬼了,见大头鬼了。可是是不是真的爱上什么人不是由你定的,你妈的,到底谁定的?到底谁管?凭什么呀?凭什么要喜欢你?凭什么?凭什么?”我想大声喊,喊醒所有的人,包括这个楼上的,父母单位的,包括学校的同学、老师,包括老流氓孔建国朱裳妈妈的老相好,喊醒所有睡着了的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在鬼哭狼嚎,自己在鬼哭狼嚎地喜欢着一个姑娘。 "
“为什么现在不是一千年以前?作屠夫的如果胳膊粗,可以象樊哙一样挥舞着杀猪刀去取人首级。如果舌头长,可以周游列国搬弄是非。哪怕阳物伟岸,也可以插进车轮,定住马车,让武则天听到谣言招进宫去。即使现在是一百年前,也能把朱裳抢上山去。过去好啊,斗殴和强奸一样,都是生存手段,现在都要受法律制裁。
现在是现在,街上有“面的”,路灯会定时熄灭定时亮起。现在能干什么呢?
“我这回真的信了,我信了还不行吗?”我听进我自己的声音突然变小,变得轻柔:“如果这辈子我能娶到朱裳,就让她屋子里的灯亮了吧!亮了我就信了。”
“让灯亮了吧。”
“亮了吧!”
那盏灯突然亮了,一点道理没有地突然亮了,在我念第三遍咒语的时候亮了。
我一路小跑,躲进我的房间里。 "
“我和张国栋认为是她的诗才太盛,但是表达能力太差,郁积在胸,变成了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
“代课语文老师仗着他的大脑袋,精通中国文人的传统绝技:牢骚与胡说八道”
“比如讲公子重耳时,至少要讲重耳的板肋与重瞳,板肋就是排骨中间没肉,连成一块。重瞳就是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天生的四眼,很吓人。如果讲台下的女学生们听得入迷,双手托腮,腮帮子白里透红,语文老师还要讲起重耳像女人珍视她们乳房一样珍视他的板肋,时常抚摸,他逃亡的时候,有个国君趁他洗澡的时候偷看了一眼他的板肋,重耳隐忍退让,当时什么也没说,等得势当上晋国国君之后,找了个借口把那个国君干掉了”
“爱念书的几个人象往常一样,屁股和椅子紧紧地吸着,复习上课记的笔记:“陕西,手巾板儿朝后。山西,朝前……”
鼻孔黑黑的男生对着同桌的眉眼傻笑:摊上新来了批水洗布的裤子,裤形不错,想不想一同去看看?
几个臭小子绕着桌椅游走玩耍,互相拍打对方的身体以示友好:又过了一节课,你是否感觉幸福? "
“还立志当采花大盗呢?扯淡。”我暗暗骂了自己一句。 "
“你说要是哥伦布有个数学老师,他能发现新大陆吗?不能细听,听多了许多欲望都会没的。不仅食欲,兴许连春梦都没得做了呢。” "
“穷文富武。文人吃饱了先想的一定是抱姑娘而不是写文章。不过,这或许是请客的真实目的呢。””
“我忽然不想上下午的政治课了,天阴了起来,我想回我的房间去。 "
“桌子的右手是扇窗子,窗子里盛了四季的风景,花开花落,月圆月缺。桌子的左手是扇门,我走进来,反手锁上,世界就被锁在了外边。
点亮灯,喝一口茶,屋里的世界便会渐渐活起来。曹操会聊起杀人越货,谈笑生死,以及如何同袁绍一起,听房,轮奸别人的新媳妇。毛姆会教我他的人生道理,最主要的一条是不要带有才气的画家或是写诗的到家里来,他们吃饱以后一定会勾引你的老婆。受尽女人宠的柳永低声哼着他的《雨霖铃》,劳伦斯喃喃地讲生命是一程残酷无比的朝圣之旅。杜牧才叹了一声“相思入骨呀”,永远长不大的马克吐温便开始一遍遍教你玩儿时的种种把戏。 "
“有些问题太难懂,仿佛上学离开妈妈,仿佛将来要将性命托给另外一个女人,仿佛现在心里喜欢上一个姑娘。小屋子太小了,容得下两个人吗?屋里的天地太大了,那个姑娘会喜欢吗?””
“我坐在桌子前,世界和自己之间是一堵墙,墙和自己之间是一盏灯,灯和自己之间是一本书。书和自己之间,是隐隐约约的朱裳的影子。”
“看得见数学老师不停翕动,唾沫细珠乱蹦的嘴,但是听不见任何声音,教室静寂无声。看得见每个人脑袋里的血管和血管里的思想,但是无法判断是邪恶还是伪善”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和我躺在一张床上的李白、柳永、杜牧之流正用阴冷而狠毒的眼神看着我,张张惨白的脸在防腐剂中浸泡了千年,显得空洞而没有意义。”
“大家富点了,钱怎么花呀?一是给自己花,有病看西医,没病看中医。”
“出去淫荡吧!康大叔说得好,包好!包好!画阴阳盂的人巨聪明,你瞧,一阴,一阳,一男一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边多的正是一方边少的。我看,人心里都有个空荡荡的洞,你怎么努力,踢球、打牌、毛片、自提,没有用,最多只能堵住半边。就象阴阳盂,男孩只有泡在女孩那儿,才能补齐那半边,才能真正实在,才能真正愉快。去吧!包好,包好。””
“再捅捅,这得自己来了,我也帮不上你。仿佛和尚讲的‘悟’,师傅说出大天去也没有用,还得自己想明白。””
“有时候想明白也没有用,事情不经就没法明白。”
“扯淡。即使有点感觉,又能怎么样呢?语文老师说:‘假如我的眼睛使你心跳,我就从你脸上移开我的目光;假如打桨激起了水波,就让我的小船离开你的岸边。’我和你不一样,我没有你挺。” 我又喝了一口酒。 "
“他怎么想起来的?”
“或许是长到时候了吧,和憋尿差不多。”
“或许是天热,气烦。””
“阳正在下沉,“为什么初生的与要下沉的总是很大?”红红的、圆圆的,仿佛某种永难愈合的伤口。”
“这是他的逻辑,不是我的逻辑,你知道我的,我没逻辑。”
“你真仗义,如果没有‘然后’的话?”
“然后咱俩把位子换过来。”
“不干。”
“只换半年。”
“免谈。不干。””
“好吧,你等好吧。我知道你瞧不上我,一入校你就让我难看,你们都看不上我,我也会让你很难看的。””
“不再是楼群间的老路了”
“朱裳后来告诉我,她脑子里浮现出那个很丑很丑的布娃娃,以及把娃娃剪成碎片的剪刀,没有继续想,重重地关上了门,转身靠在门框上,泪如泉涌。”
“我在朱裳关门的一瞬间,瞥见她身后,阳台上,她白地粉花的内裤随风飘摇。”
“我尤其喜欢评论的最后一段,感觉自己象是巫师,具备了盅惑人心的超能力。”
" 最不喜欢一个人吃饭。在赶小说的过程中偶尔和几个小说中的原型吃饭,最后都是对着窗外的冬天,喝一口燕京纯生,感叹“人生苦短,还是喜欢干点什么就趁早干点什么”
“灯市口大街北边有个打折书店,新书堆着卖,跟冬储大白菜似的,汗牛冲栋,从地板一直瘀到屋顶,王小波的全套四大本文集才卖二十元。当时一个恍惚,如五雷轰顶,信心顿失,这里面多少垃圾呀?五百年后有多少书还有人读呀?在这种认识下,要多大的牛逼和多大的自大狂才能撅着屁股写成十几万字,然后印在干干净净的白纸上,糟践好些用来制造白纸的树木和花花草草。想起那个日本鬼才芥川龙之介,怀疑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打开阁楼的窗户,向着虚空,大声叫喊:“我是天才。”最后还是没用,三十五岁服了安眠药死掉。”
“桃花落尽子满枝”,过去操场上领操的校花,如今正考虑什么时候破坏国家政策生第二胎,要不要自己开个幼儿园。何苦打着记录生命经验的旗号,再意淫人家一遍?”
“于是热烈地盼望再有几个长假,把我不能不落在纸上的东西写完。写完了,心里面就该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了吧?再见老相好也能心如古井水,没有一丝波澜。于是热烈地盼望着没有写作冲动的那一天,然后就号称自己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一个字也不写了,就像热烈地盼望着阳痿的到来。
野史说,江淹才尽后,过着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幸福生活。我愿意相信。”